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论诗术》是现存亚里士多德讲课稿中最难释读的文本,晦涩到难以理解的地步。绎读《论诗术》第2、3章,可知它讨论的不是如今所谓的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从如何作诗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生活方式有德性高低之分。
 。《论诗术》第2、3章讨论作诗的品质差异,涉及模仿的对象不同。这一差异明显比第1章所讨论的赖以模仿的东西不同更重要。 第2章篇幅很短,亚里士多德一上来就说:
。《论诗术》第2、3章讨论作诗的品质差异,涉及模仿的对象不同。这一差异明显比第1章所讨论的赖以模仿的东西不同更重要。 第2章篇幅很短,亚里士多德一上来就说:  既然模仿者模仿行为着的人,既然这些人必然要么高尚,要么低俗——性情几乎总是随着这些而来,因为每个人的性情都在坏得性②和好德性上见出差别,那么,模仿者模仿的那些[行为者]与我们相比要么更好、要么更坏,要么像我们如此这般…… 这个句子显然是在说伦理学的事情,而非诗学的事情。“模仿者模仿
既然模仿者模仿行为着的人,既然这些人必然要么高尚,要么低俗——性情几乎总是随着这些而来,因为每个人的性情都在坏得性②和好德性上见出差别,那么,模仿者模仿的那些[行为者]与我们相比要么更好、要么更坏,要么像我们如此这般…… 这个句子显然是在说伦理学的事情,而非诗学的事情。“模仿者模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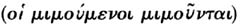 行为着的人”重叠用了两次模仿,显得累赘,有的西文译本(如哈迪的法译本)把“模仿”改译为répresentent[再现]。宾语“行为着的人”与下一分句的“这些人”显然有连带关系,都是宾格,表明作为模仿者的诗人与被模仿者即诗作中的人物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关系。被模仿者的德性“必然”有高低之分,似乎模仿者即诗人的德性只会是高的,因为,高的才可以既模仿高的也模仿低的,低的绝无可能模仿高的。然而,事实上模仿者的德性同样有高低之分,这意味着:作诗的模仿也可能是低的模仿低的。无论如何,作为模仿者的诗人与被模仿的诗中人物都是行为者,凡行为都有德性高低之分,或高或低取决于行为者的性情德性,是一个人的性情使然。模仿者的德性高低之分,同样取决于模仿者的性情德性。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常识,除非如今念文科的从未读过《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模仿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反过来说,就性质而言,行为着的人本身的行为就是模仿,或者说“行为着的人”是生活中的模仿者。从而,“模仿者模仿行为着的人”也可以读作“行为着的人模仿行为着的人”,或者“模仿者模仿模仿者”。换言之,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关系颇为复杂。由此来看,第一个分句的“模仿者模仿”这一重叠说法意味深长,不可用“再现”一类说法代替,宁可死译。事实上,“要么高尚,要么低俗”不仅可以用在被模仿者身上,同样可以用在模仿者诗人身上。只不过高的模仿低的容易——可以装样子,低的模仿高的就很难,因为受制于性情品质的限定。莱辛说:我们没法模仿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的德性品质太高。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坏人模仿好人总学不像,或者说最终难免被识破,但好人模仿坏人就不容易看出来了,这种情形最为可怕——马基雅维利是堕落的天使,这种天使最难对付。 “要么高尚,要么低俗”——“高尚”和“低俗”都是道德语汇,但在《论诗术》中却非常重要。就希腊语原文的义项而言,两个语词的含义都有好些,没法用一个现代语词来对应。现有的中译本大多把
行为着的人”重叠用了两次模仿,显得累赘,有的西文译本(如哈迪的法译本)把“模仿”改译为répresentent[再现]。宾语“行为着的人”与下一分句的“这些人”显然有连带关系,都是宾格,表明作为模仿者的诗人与被模仿者即诗作中的人物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关系。被模仿者的德性“必然”有高低之分,似乎模仿者即诗人的德性只会是高的,因为,高的才可以既模仿高的也模仿低的,低的绝无可能模仿高的。然而,事实上模仿者的德性同样有高低之分,这意味着:作诗的模仿也可能是低的模仿低的。无论如何,作为模仿者的诗人与被模仿的诗中人物都是行为者,凡行为都有德性高低之分,或高或低取决于行为者的性情德性,是一个人的性情使然。模仿者的德性高低之分,同样取决于模仿者的性情德性。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常识,除非如今念文科的从未读过《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模仿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反过来说,就性质而言,行为着的人本身的行为就是模仿,或者说“行为着的人”是生活中的模仿者。从而,“模仿者模仿行为着的人”也可以读作“行为着的人模仿行为着的人”,或者“模仿者模仿模仿者”。换言之,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关系颇为复杂。由此来看,第一个分句的“模仿者模仿”这一重叠说法意味深长,不可用“再现”一类说法代替,宁可死译。事实上,“要么高尚,要么低俗”不仅可以用在被模仿者身上,同样可以用在模仿者诗人身上。只不过高的模仿低的容易——可以装样子,低的模仿高的就很难,因为受制于性情品质的限定。莱辛说:我们没法模仿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的德性品质太高。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坏人模仿好人总学不像,或者说最终难免被识破,但好人模仿坏人就不容易看出来了,这种情形最为可怕——马基雅维利是堕落的天使,这种天使最难对付。 “要么高尚,要么低俗”——“高尚”和“低俗”都是道德语汇,但在《论诗术》中却非常重要。就希腊语原文的义项而言,两个语词的含义都有好些,没法用一个现代语词来对应。现有的中译本大多把 译作“严肃”,本文认为值得译作“高尚”,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说法将
译作“严肃”,本文认为值得译作“高尚”,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说法将 与
与 [低俗]对举③。这两个语词有如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的两个刻度,其间还可以划分出很多更为细小的德性区分,毕竟,人的性情德性有巨大而又细微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细致讨论的就是这些差异,而且由低向高推移。然而,性情是不可见的,惟有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可以见出其性情,因此只能模仿“行为着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一上来没有说模仿性情。反过来看,模仿者也如此:诗人、作家的性情同样是看不见的,人们通过诗人的作诗行为才可以见出其性情。张爱玲的性情本来是不可见的,但她的小说让她的性情表露无遗。正如不可见的诗术本身只有通过具体的诗术样式才可见,只有通过可见的作诗样式才能见出诗人自身的性情。性情的隐与显可以看作诗术本身与诗术样式的关系:诗人或作家的模仿行为本身才显出其性情的不可见之隐——“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由此来看,《论诗术》第1章在举例时提到各种各样的模仿者就显得意味深长了:索弗戎没法与苏格拉底相比,凯瑞蒙没法与荷马相比。
[低俗]对举③。这两个语词有如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的两个刻度,其间还可以划分出很多更为细小的德性区分,毕竟,人的性情德性有巨大而又细微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细致讨论的就是这些差异,而且由低向高推移。然而,性情是不可见的,惟有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可以见出其性情,因此只能模仿“行为着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一上来没有说模仿性情。反过来看,模仿者也如此:诗人、作家的性情同样是看不见的,人们通过诗人的作诗行为才可以见出其性情。张爱玲的性情本来是不可见的,但她的小说让她的性情表露无遗。正如不可见的诗术本身只有通过具体的诗术样式才可见,只有通过可见的作诗样式才能见出诗人自身的性情。性情的隐与显可以看作诗术本身与诗术样式的关系:诗人或作家的模仿行为本身才显出其性情的不可见之隐——“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由此来看,《论诗术》第1章在举例时提到各种各样的模仿者就显得意味深长了:索弗戎没法与苏格拉底相比,凯瑞蒙没法与荷马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