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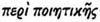 这个书名被译作《诗学》“不以为然”,因为“近代西语poetic,poétique只是音译,等于未译”①。左景权先生反对把书名译作《诗学》的理由有二:1.希腊语的
这个书名被译作《诗学》“不以为然”,因为“近代西语poetic,poétique只是音译,等于未译”①。左景权先生反对把书名译作《诗学》的理由有二:1.希腊语的 与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有实质变化,按字面去译,反不如《创作论》为佳”;2.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谋篇布局精心剪裁的,是否诗体还在其次”(同上)。 如果左景权先生真的是古希腊学家,这些说法是否确实出自左先生手笔,让人犯疑。因为,第一条理由将poetry或poésie视为古希腊语动词不定式
与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有实质变化,按字面去译,反不如《创作论》为佳”;2.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谋篇布局精心剪裁的,是否诗体还在其次”(同上)。 如果左景权先生真的是古希腊学家,这些说法是否确实出自左先生手笔,让人犯疑。因为,第一条理由将poetry或poésie视为古希腊语动词不定式 (做、作)的对译,显然不对,应该是
(做、作)的对译,显然不对,应该是 ,尽管这个名词派生自动词
,尽管这个名词派生自动词 ,语义却并不等于
,语义却并不等于 。第二条理由也是错的,因为,倘若“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是否诗体还在其次”的说法成立,亚里士多德在讲稿中说到诗的“编织不应像纪事
。第二条理由也是错的,因为,倘若“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是否诗体还在其次”的说法成立,亚里士多德在讲稿中说到诗的“编织不应像纪事 ”(1459a17,亦参1451b12)就无从解释。何况,明摆着的文本事实是,亚氏在讲稿中主要讨论的是“有体之诗”(
”(1459a17,亦参1451b12)就无从解释。何况,明摆着的文本事实是,亚氏在讲稿中主要讨论的是“有体之诗”( ),而非“大块文章”(
),而非“大块文章”( )。 左先生的这封私信后来刊发在一家学刊上,他的看法得到刘以焕先生热烈认同。在1994年发表的专文(今收入氏著《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前揭)中,刘以焕先生为左先生的第一条理由作了如下补充:
)。 左先生的这封私信后来刊发在一家学刊上,他的看法得到刘以焕先生热烈认同。在1994年发表的专文(今收入氏著《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前揭)中,刘以焕先生为左先生的第一条理由作了如下补充: 来自
来自 (意为“做、创造”),言下之意,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显然不是“做、创造”;反过来说,“诗学”一词“在汉语文中指写诗论诗的学问,而所写所论的诗,大多是篇幅不长的古体或近体诗”,与亚里士多德所论不合。“若将亚氏的
(意为“做、创造”),言下之意,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显然不是“做、创造”;反过来说,“诗学”一词“在汉语文中指写诗论诗的学问,而所写所论的诗,大多是篇幅不长的古体或近体诗”,与亚里士多德所论不合。“若将亚氏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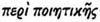 翻译为《诗学》,不仅不确切,而且会产生误导”,因此,刘以焕先生主张,“不能迁就原来的约定俗成,应将其订正,迻译为《创作论》为是”;至于何谓“创作”,他明确说明:“一指创造文艺作品,二指文艺作品本身。”② 王士仪译本的书名译作《创作学》倒不一定是受到上述两位启发,因为,王先生自己的大著《论亚里士多德〈创作学〉》早在1990年就已经出版(台北:里仁版)。可以想见的是,王先生改《诗学》为《创作学》的理由,可能与左、刘两位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刘以焕先生明确提出的两条理由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主张,不当以后世之词义(比如poetry或poésie)绳古之词义[比如
翻译为《诗学》,不仅不确切,而且会产生误导”,因此,刘以焕先生主张,“不能迁就原来的约定俗成,应将其订正,迻译为《创作论》为是”;至于何谓“创作”,他明确说明:“一指创造文艺作品,二指文艺作品本身。”② 王士仪译本的书名译作《创作学》倒不一定是受到上述两位启发,因为,王先生自己的大著《论亚里士多德〈创作学〉》早在1990年就已经出版(台北:里仁版)。可以想见的是,王先生改《诗学》为《创作学》的理由,可能与左、刘两位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刘以焕先生明确提出的两条理由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主张,不当以后世之词义(比如poetry或poésie)绳古之词义[比如 (做、创造)];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汉语的“创作”来翻译
(做、创造)];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汉语的“创作”来翻译 ,又恰恰是在以后世之词义绳古之词义。我国古人习用单字而非双字,“创”和“作”在古汉语中是两个字,联属用法出现较晚。“创”的本义为“始造、首创”(《广雅·释诂》:“创,……始也”);“作”这个字有二十几个义项,本义是“兴起、发生”(《说文》:“作,起也”),然后有“建造、制作”之意(《尔雅·释言》:“作、造,为也”),所谓“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即便出现“创作”联署的用法后,意思仍首先是“制造、建造”:所谓“创作巨石礮来献”,所谓“创作兵车阵图刀楯之属,皆有法”等等。“创作”联署用于“写作”或所谓“创作文艺作品”,古书中并不多见,倒是盛行于今世③。
,又恰恰是在以后世之词义绳古之词义。我国古人习用单字而非双字,“创”和“作”在古汉语中是两个字,联属用法出现较晚。“创”的本义为“始造、首创”(《广雅·释诂》:“创,……始也”);“作”这个字有二十几个义项,本义是“兴起、发生”(《说文》:“作,起也”),然后有“建造、制作”之意(《尔雅·释言》:“作、造,为也”),所谓“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即便出现“创作”联署的用法后,意思仍首先是“制造、建造”:所谓“创作巨石礮来献”,所谓“创作兵车阵图刀楯之属,皆有法”等等。“创作”联署用于“写作”或所谓“创作文艺作品”,古书中并不多见,倒是盛行于今世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