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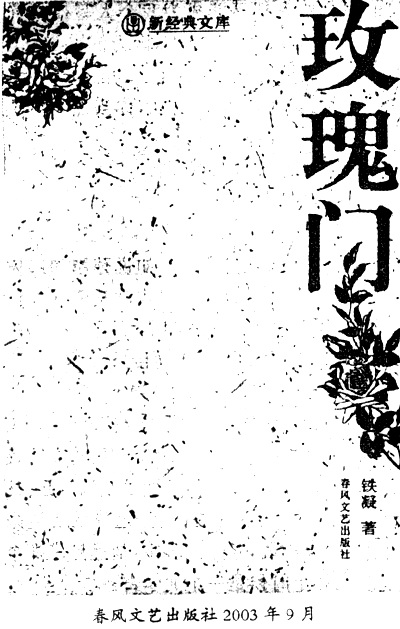 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强调了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二者缺一不可 。身体是说出写作者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在场,他是出现在写作里面,不是跟写作脱离关 系的。写作者作为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想 象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惟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另外一 个要素是语言,所谓“语言史”,是说写作者用语言描述、记录和想象了自己的身体在 经历这个时代的景象。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照样,离开 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就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是同 构在一起的。因此,真正伟大的作家,都能将身体语言化,语言身体化,使语言具有自 己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 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 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基本印象(注:参见于坚、谢有顺《写 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当然,身体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能作这样机械的理 解,只是,作为个人语言史的写作,如果没有身体的参与,仅凭知识、幻想,确实是难 以获得真实的生命感受的。 但从身体出发,也可能发展出一种身体迷信,使写作沉迷于一种身体(甚至肉体)乌托 邦之中。已经有一些作家在为身体(甚至肉体)乌托邦而写作,他们忽视了语言对身体的 制约,结果写作就成了性爱感受和肉体经验的单一展示,丧失了基本的理想,也丧失了 生命的基本信念。因此,我不想再在这个层面上使用“身体写作”这个说法(因为它已 经变质),而更愿意援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这一判断,强化身体的在场,也强调 语言的创造性。前者是经验的,后者则是伦理的——语言伦理不同于一般的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注重价值判断,而语言伦理则注重呈现生存的状态,注重理解个体的生活。我 认为最好的写作,就应该既是经验的,又是伦理的,比如卡夫卡的写作,就是经验与伦 理相统一的典范。中国目前的写作状况,有两种模式值得警惕,一种是将身体不断肉体 化,从而导致写作经验彻底私秘化和性爱化,写作成了一种庸俗的宣泄;一种是抽空身 体细节,忽视身体在场时的生活景象,一味地经营语言的修辞效果、叙事的技术成分, 结果,写作成了一种知识的演绎,或者修辞的表演,语言也就不再是有身体的、活泼的 语言,而成了一堆死去的词语,一个生命的废墟。 如何使身体语言化以及语言身体化,就成了写作真正的难度之一。身体若和语言脱节 ,势必产生写作的陷阱,进而伤害写作的尊严和光辉。——说到写作的尊严,它似乎是 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其实,写作的确是有尊严和光辉的,失去了这个维度,写作的品质 总是可疑。但我们不要一说到尊严,就总是想到形而上、理想、意义、价值这些概念, 其实,身体何尝没有尊严,日常生活又何尝没有尊严!生命的光辉是内在而坚实的,并 非一些空洞的概念所能代替。现在的困境是,总有一些作家,或者完全否认身体和日常 生活的地位,把它们直接斥之为堕落或庸俗的代名词;或者把身体和日常生活当做写作 的全部经验和存在的终极,拒绝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写作,完全取消了写作 的伦理性——这种危险的写作方式,在当下还有泛滥的趋势,可见,文学界对身体和日 常生活的误解还在加深。 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写作也是一种语言伦理,似乎就显得尤其必要。身体作为一种经 验性的在场,需要经过语言伦理的检查和确证,才能抵达写作的腹地;泛滥身体经验而 忽视语言伦理的写作,最终必将发展成为践踏身体和精神的失败的写作。 就写作而言,身体伦理的本质就是语言伦理,而语言伦理学即叙事伦理学——这一伦 理诉求,对于小说写作,是内在、隐秘而重要的维度。关于叙事伦理学,刘小枫先生有 过精彩的表述: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 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 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 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 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虚气。……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 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 渊。……叙事伦理学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人生命的悖论深渊厮守在一起, 而不是像理性伦理学那样,从个人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 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 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 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4—5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9年。)
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强调了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二者缺一不可 。身体是说出写作者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在场,他是出现在写作里面,不是跟写作脱离关 系的。写作者作为一个有身体的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想 象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惟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另外一 个要素是语言,所谓“语言史”,是说写作者用语言描述、记录和想象了自己的身体在 经历这个时代的景象。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照样,离开 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就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是同 构在一起的。因此,真正伟大的作家,都能将身体语言化,语言身体化,使语言具有自 己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 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 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基本印象(注:参见于坚、谢有顺《写 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当然,身体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能作这样机械的理 解,只是,作为个人语言史的写作,如果没有身体的参与,仅凭知识、幻想,确实是难 以获得真实的生命感受的。 但从身体出发,也可能发展出一种身体迷信,使写作沉迷于一种身体(甚至肉体)乌托 邦之中。已经有一些作家在为身体(甚至肉体)乌托邦而写作,他们忽视了语言对身体的 制约,结果写作就成了性爱感受和肉体经验的单一展示,丧失了基本的理想,也丧失了 生命的基本信念。因此,我不想再在这个层面上使用“身体写作”这个说法(因为它已 经变质),而更愿意援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这一判断,强化身体的在场,也强调 语言的创造性。前者是经验的,后者则是伦理的——语言伦理不同于一般的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注重价值判断,而语言伦理则注重呈现生存的状态,注重理解个体的生活。我 认为最好的写作,就应该既是经验的,又是伦理的,比如卡夫卡的写作,就是经验与伦 理相统一的典范。中国目前的写作状况,有两种模式值得警惕,一种是将身体不断肉体 化,从而导致写作经验彻底私秘化和性爱化,写作成了一种庸俗的宣泄;一种是抽空身 体细节,忽视身体在场时的生活景象,一味地经营语言的修辞效果、叙事的技术成分, 结果,写作成了一种知识的演绎,或者修辞的表演,语言也就不再是有身体的、活泼的 语言,而成了一堆死去的词语,一个生命的废墟。 如何使身体语言化以及语言身体化,就成了写作真正的难度之一。身体若和语言脱节 ,势必产生写作的陷阱,进而伤害写作的尊严和光辉。——说到写作的尊严,它似乎是 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其实,写作的确是有尊严和光辉的,失去了这个维度,写作的品质 总是可疑。但我们不要一说到尊严,就总是想到形而上、理想、意义、价值这些概念, 其实,身体何尝没有尊严,日常生活又何尝没有尊严!生命的光辉是内在而坚实的,并 非一些空洞的概念所能代替。现在的困境是,总有一些作家,或者完全否认身体和日常 生活的地位,把它们直接斥之为堕落或庸俗的代名词;或者把身体和日常生活当做写作 的全部经验和存在的终极,拒绝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写作,完全取消了写作 的伦理性——这种危险的写作方式,在当下还有泛滥的趋势,可见,文学界对身体和日 常生活的误解还在加深。 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写作也是一种语言伦理,似乎就显得尤其必要。身体作为一种经 验性的在场,需要经过语言伦理的检查和确证,才能抵达写作的腹地;泛滥身体经验而 忽视语言伦理的写作,最终必将发展成为践踏身体和精神的失败的写作。 就写作而言,身体伦理的本质就是语言伦理,而语言伦理学即叙事伦理学——这一伦 理诉求,对于小说写作,是内在、隐秘而重要的维度。关于叙事伦理学,刘小枫先生有 过精彩的表述: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 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 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 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 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虚气。……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 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 渊。……叙事伦理学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人生命的悖论深渊厮守在一起, 而不是像理性伦理学那样,从个人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 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 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 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4—5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