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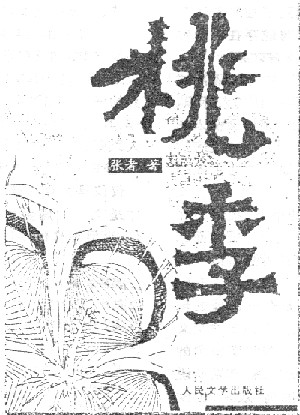 一、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根据齐格蒙·鲍曼的研究,“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 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 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职业 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 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进程, 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 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 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 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尺度。(注:齐格蒙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1—2页、第221 —222页、第223—225页、第214页,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鲍 曼这种对知识分子身份和意义的理解,参照的显然还是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知识 /权利”之共生现象这个现代性特征紧密相联,它更多的是指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 但在知识分子漫长的思想史和生活史中,真正处于这种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大多数时候,由于权力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压制,导致许多知识分子都随波逐流,无 所事事,有的还成了权力的附庸,使他们身上本应有的责任、理想和批判精神成了一句 空谈。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就曾尖锐地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 随大流的。在前苏联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统治中,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和萧斯塔柯维奇 都不能始终坚定。……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注: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 《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载《天涯》1998年第5期。)难 怪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在备受尊敬的同时,也遭遇到了猛烈的嘲讽和指责。美国第34届 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说过:“我听说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 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这话虽是借用,但里 面的鄙薄之情可见一斑。而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则在《知识分子》(注:保罗·约翰 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该书因对知识分 子的尖锐批判而引起广泛的影响和争议,中文版也不例外。)一书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 更加极端的攻击:“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物所能提供的合理见 解,至少不亚于知识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些义愤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 分子形象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他们不再被看作是神圣的代言人角 色,也不再被认为是真理和道德的转播者。 这种情形在中国就更复杂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知识分子思想传统的国度,这一 点,你只要看中国的典籍记载里,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或“士大夫”(其实就是古代 的知识分子)都是庄严而富有使命感的,就可略知一二。尤其是从孔子开始,古代的士 人就多以“道”自任,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虽然“道”各不同,但在要求士 人代表“道”这点上却是一样的。而春秋战国恰好又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 不再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孔子曾斥之为:“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他的意思 是说,既然统治阶级不能承担“道”,“道”便要转由明白“礼意”的“士”来承担, 反过来说,现在“天下无道”,“士”就不能不起来批评、抗议一切丑陋的、不好的现 象。所以,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都竭力强调“士志于道”、“士尚志”、“ 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超越精神,希望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良 心,并批判现实世界。按理说,中国“士人”(知识分子)有至少两千多年这样的“明道 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应可发展出一套很完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可是,为什 么直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意识一直无法在中国得到真正的确认和实践呢? 尽管到了近代以后,也曾有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国民革命等,它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进程意义深远,但就知识分子自身的性格而言,其 实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余英时先生对此多有研究,他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一文里说:“中国有一个顽固的道德传统。但是和西方相 对照,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终嫌不足。中国人对知识的看法过于偏重在 实用方面,因此知识本身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并未构成一独立自足的领域。这一点自然也 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知识和道德之间必须取得平衡,这在今天已是有识之士所 共同承认的。”(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月第一版。)另外,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良心的士人(知识分子),绝大多 数尊崇的是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儒家型知识分子,一直来都坚持“道”高于“势”(此 观点由孟子正式提出,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 也”),坚持用“道”来“纲纪世界”;而道家型知识分子则更强调个体的自由,在此 基础上,也坚持用他们的道(无论是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还是明代的李贽,“道” 的内涵都多为“自然”的观念)来批判“名教”和“礼教”。这些观念今天看来,积极 作用显著,可局限性也一目了然。
一、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根据齐格蒙·鲍曼的研究,“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 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 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职业 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 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进程, 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 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 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 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尺度。(注:齐格蒙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1—2页、第221 —222页、第223—225页、第214页,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鲍 曼这种对知识分子身份和意义的理解,参照的显然还是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知识 /权利”之共生现象这个现代性特征紧密相联,它更多的是指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 但在知识分子漫长的思想史和生活史中,真正处于这种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并不多, 大多数时候,由于权力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压制,导致许多知识分子都随波逐流,无 所事事,有的还成了权力的附庸,使他们身上本应有的责任、理想和批判精神成了一句 空谈。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就曾尖锐地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 随大流的。在前苏联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统治中,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和萧斯塔柯维奇 都不能始终坚定。……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注: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 《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载《天涯》1998年第5期。)难 怪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在备受尊敬的同时,也遭遇到了猛烈的嘲讽和指责。美国第34届 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说过:“我听说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 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这话虽是借用,但里 面的鄙薄之情可见一斑。而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则在《知识分子》(注:保罗·约翰 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该书因对知识分 子的尖锐批判而引起广泛的影响和争议,中文版也不例外。)一书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 更加极端的攻击:“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物所能提供的合理见 解,至少不亚于知识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些义愤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 分子形象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他们不再被看作是神圣的代言人角 色,也不再被认为是真理和道德的转播者。 这种情形在中国就更复杂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知识分子思想传统的国度,这一 点,你只要看中国的典籍记载里,我们通常所说的“士”或“士大夫”(其实就是古代 的知识分子)都是庄严而富有使命感的,就可略知一二。尤其是从孔子开始,古代的士 人就多以“道”自任,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虽然“道”各不同,但在要求士 人代表“道”这点上却是一样的。而春秋战国恰好又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 不再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孔子曾斥之为:“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他的意思 是说,既然统治阶级不能承担“道”,“道”便要转由明白“礼意”的“士”来承担, 反过来说,现在“天下无道”,“士”就不能不起来批评、抗议一切丑陋的、不好的现 象。所以,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都竭力强调“士志于道”、“士尚志”、“ 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超越精神,希望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良 心,并批判现实世界。按理说,中国“士人”(知识分子)有至少两千多年这样的“明道 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应可发展出一套很完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可是,为什 么直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意识一直无法在中国得到真正的确认和实践呢? 尽管到了近代以后,也曾有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国民革命等,它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进程意义深远,但就知识分子自身的性格而言,其 实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余英时先生对此多有研究,他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一文里说:“中国有一个顽固的道德传统。但是和西方相 对照,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终嫌不足。中国人对知识的看法过于偏重在 实用方面,因此知识本身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并未构成一独立自足的领域。这一点自然也 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知识和道德之间必须取得平衡,这在今天已是有识之士所 共同承认的。”(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月第一版。)另外,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良心的士人(知识分子),绝大多 数尊崇的是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儒家型知识分子,一直来都坚持“道”高于“势”(此 观点由孟子正式提出,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 也”),坚持用“道”来“纲纪世界”;而道家型知识分子则更强调个体的自由,在此 基础上,也坚持用他们的道(无论是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还是明代的李贽,“道” 的内涵都多为“自然”的观念)来批判“名教”和“礼教”。这些观念今天看来,积极 作用显著,可局限性也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