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社会引发了人们对生存、发展的新思考,也造就了作家、艺术家对生成文艺的意义与价值的新探索。尽管世纪末文学艺术的雅、俗分流,文体形态与写作方式多元互渗的复杂景观,引起了广大读者或褒或贬的议论,但有一点是不应当怀疑的,那就是多数作家、艺术家在更新文艺观念,探求新的文体与写作方式时,并没有放弃文艺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追求与承诺。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洗礼中更认识到现代化的发展决不应该以牺牲人文理性为代价;越是一个物质繁荣、科学昌盛的时代,人们愈益感到灵魂栖居与精神家园建设的迫切。 一 追溯20世纪后20年改革开放中的文艺嬗变,不难发现,作家、艺术家对生成文艺的意义与价值的新探索,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观念更新和文体范式的多元试验,正是个性化审美意识的不断自觉,打破了文艺审美创造的一体化格局,遂促成了作家、艺术家以语言、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重新认识文艺的特质与规律,不断拓展文艺意义与价值的生成空间。在这一方面,小说观念与文体的多元探索是走在其它文艺样式的前列的,值得认真总结。 长期以来,语言、形式一直被看成实现文学目的的手段。尤其在政治一元话语消解文学的多元话语形态的年代,文学语言与形式更是服务于政治内容的直接工具。只是随着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获得解放,一些作家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拓展艺术感觉、打破内容与形式的传统法则中得到启示之后,才进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多元文学意义生成与语言、形式的内在关系。对此,老作家汪曾祺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可有可无的。”(注: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对语言、形式的重新认识,反映了文学理念的变革、拓展。汪曾祺所代表的新理念,是把语言视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小说的本体地位,甚至强调指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自身的小说创作,恰好印证了他的文学语言观。 其实,在80年代那些视语言为文学(小说)之根本的作家中,重视语言、形式的文学创新又是呈现多元化的。如果说刘索拉等一批小说较早被称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的试验,还没有把形式的变革提到文学(小说)本体的高度,只是类似现代主义某些流派的形式翻新的话;那么,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北村等作家的小说语言、形式试验,则夹杂后现代语言游戏的某些特征。“相对地说,现代主义的焦虑、孤独和反讽隐藏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后现代主义却是在丧失深度的同时滑行在价值平面上。”“对于马原这批作家说来,叙事是他们从事游戏的乐园。从拼贴、中断到戏仿、自我指涉,他们的叙事冒险层出不穷。”(注:南帆:《隐蔽的成规》,。)从而表明了他们对传统文学价值的历史生成与现代主义的主体神话已失去信心,转而在叙事游戏之中尝试种种话语的可能。与此同时,王朔以调侃为特质的语言、形式,虽也滑行于价值平面上,却不同于叙事游戏的“文本欢悦”,倒是成了狂欢化的嬉戏。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小说和诗歌,则以解构新启蒙话语和“朦胧诗”精英独白的意义为能事。然而,他们所追求的“自我”,却只是个人重新占领身体的感受,而他们所以张扬世俗的口语,则因为这种语言恰好照顾到这种“自我”的身心,即带有强烈的私生活心理。总之,比较隐蔽的个性化独语,构成了“新生代”语言的表现方式。 可见,在近20年多元化的文学语言变革中,凸显了一部分作家的现代文学观念对语言的意义的强调,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学正是凭借形式使自己从客观现实和主体心灵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客观性的话语存在,成了一种超越主体与现实的“他性”。不仅如此,由于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的创造,而审美又主要是涉及形式的,没有感性形式也就谈不上审美,因而不可忽视文学形式的审美追求与建构,及其对生成文学价值的多种可能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创新意识和开放意识的带动下,不少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文学意义生成的新认识。 首先,作家对文学审美价值创造(生产)规律的认识,超越了再现论和表现论二元对立的视域。因为现实主义偏重于再现外在世界的宏大叙事与表现主义偏重于渲泄心灵世界的个体化叙事都对文学的意义生成造成缺陷,忽视了文学探索与表现人生的复杂、多维的空间。再现论强调典型化的规律,要求文学反映现实应通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具体(个别)体现普遍(多数),其语言、形式的规范也必然使个体化话语消融于公共性的宏大叙事之中;而表现论则突出个性化,重视个体自我情感体验与语言的传达,但其情感化的形式又往往被封闭于文本内部。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便把文学的形式化原则定位于主体和客体性相互交融、互动的多维度的审美建构的基础上,不仅视文学的形式化为审美意义的物化过程,更看成是审美价值生成的内在机制,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始终;先是对象客体获得主观心灵的形式(形式心灵化),尔后是主观心灵的外在表现获得客观形式(心灵形式化,即物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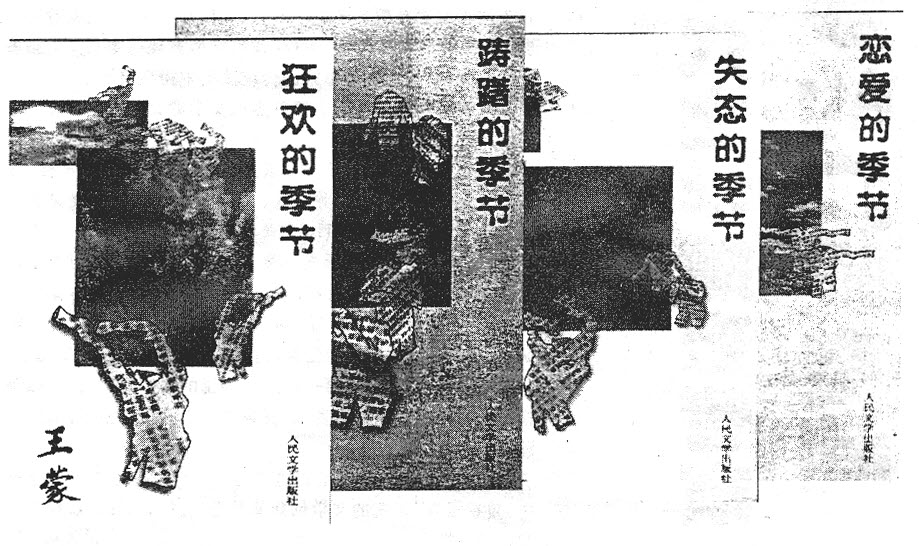
坚持这个原则,文学在生成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纯粹的客体性原则,即要求文学模仿、复制对象,比客体对象的形式法则要求艺术形式创造的偏颇;又可以超越纯粹主体性原则,因为纯粹主体性的产物是纯粹个人的、偶然性的,没有必然性、普遍性的,个人的感性形式与普遍有效性的形式法则相悖离。对此,作家王蒙在创作中早有所悟,他在《在伊犁·后记》中曾说:“真正好的小说,既是小说,也是别的什么。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悠思。”他本人在90年代前后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季节系列”的四部力作《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既保留了现实主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的构架,又吸取了现代主义善于探求心灵流变,从人物心理的常态与变态的交互描述中揭示现代人命运变幻的写作方式,其中所运用的调侃与反讽、雅俗杂糅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话语,更凸现作家个体生命体验者和叙事者的书写风格与文体特征,而不是以既往的呐喊者或启蒙者的社会代言者的姿态显现。尤其是《狂欢的季节》的文体范式,几乎越出了传统小说的边界,走向散文化的随感、议论的多种话语创造,充分展现了作家汪洋恣肆的人生感悟与波诡云谲的情感世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曾经引起重大争议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所以越来越显出其恒久的艺术魅力,就因为作家陈忠实在反思既往的历史行程时,“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注: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作者正是从主体性(现代意义的观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现实生成)的对话互动中写出了新意,写出了充满矛盾性、复杂性的历史画卷,写出了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新历史小说的文体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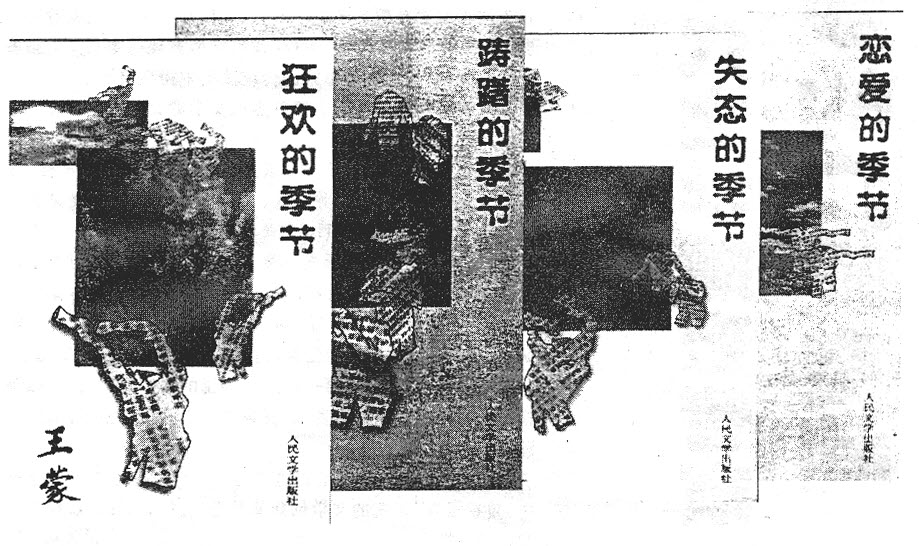 坚持这个原则,文学在生成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纯粹的客体性原则,即要求文学模仿、复制对象,比客体对象的形式法则要求艺术形式创造的偏颇;又可以超越纯粹主体性原则,因为纯粹主体性的产物是纯粹个人的、偶然性的,没有必然性、普遍性的,个人的感性形式与普遍有效性的形式法则相悖离。对此,作家王蒙在创作中早有所悟,他在《在伊犁·后记》中曾说:“真正好的小说,既是小说,也是别的什么。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悠思。”他本人在90年代前后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季节系列”的四部力作《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既保留了现实主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的构架,又吸取了现代主义善于探求心灵流变,从人物心理的常态与变态的交互描述中揭示现代人命运变幻的写作方式,其中所运用的调侃与反讽、雅俗杂糅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话语,更凸现作家个体生命体验者和叙事者的书写风格与文体特征,而不是以既往的呐喊者或启蒙者的社会代言者的姿态显现。尤其是《狂欢的季节》的文体范式,几乎越出了传统小说的边界,走向散文化的随感、议论的多种话语创造,充分展现了作家汪洋恣肆的人生感悟与波诡云谲的情感世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曾经引起重大争议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所以越来越显出其恒久的艺术魅力,就因为作家陈忠实在反思既往的历史行程时,“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注: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作者正是从主体性(现代意义的观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现实生成)的对话互动中写出了新意,写出了充满矛盾性、复杂性的历史画卷,写出了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新历史小说的文体范式。
坚持这个原则,文学在生成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中,就可以避免纯粹的客体性原则,即要求文学模仿、复制对象,比客体对象的形式法则要求艺术形式创造的偏颇;又可以超越纯粹主体性原则,因为纯粹主体性的产物是纯粹个人的、偶然性的,没有必然性、普遍性的,个人的感性形式与普遍有效性的形式法则相悖离。对此,作家王蒙在创作中早有所悟,他在《在伊犁·后记》中曾说:“真正好的小说,既是小说,也是别的什么。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悠思。”他本人在90年代前后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季节系列”的四部力作《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既保留了现实主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的构架,又吸取了现代主义善于探求心灵流变,从人物心理的常态与变态的交互描述中揭示现代人命运变幻的写作方式,其中所运用的调侃与反讽、雅俗杂糅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话语,更凸现作家个体生命体验者和叙事者的书写风格与文体特征,而不是以既往的呐喊者或启蒙者的社会代言者的姿态显现。尤其是《狂欢的季节》的文体范式,几乎越出了传统小说的边界,走向散文化的随感、议论的多种话语创造,充分展现了作家汪洋恣肆的人生感悟与波诡云谲的情感世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曾经引起重大争议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所以越来越显出其恒久的艺术魅力,就因为作家陈忠实在反思既往的历史行程时,“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注: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作者正是从主体性(现代意义的观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现实生成)的对话互动中写出了新意,写出了充满矛盾性、复杂性的历史画卷,写出了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和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新历史小说的文体范式。